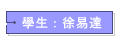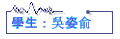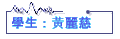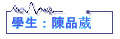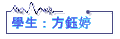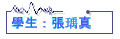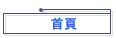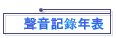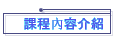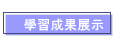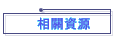|
台北北管八大軒社-共樂軒之1926年間錄音 演奏曲「遊醬令與連清讚」與子弟戲「吳漢殺妻」 |
|---|
|
台北共樂軒 大正元年(1912),台北知名北管團體靈安社部分子弟因意見不合,出來另組共樂軒。子弟多由生意人組成,亦有道士參與。大正、昭和年代,與靈安社常拼館,如每次共樂軒出陣時,展示用金子打造的三角旗,靈安社便不甘示弱的馬上訂製風帆,上鋪十角銀錢,及金子打造的旗幟。1923年,裕仁太子訪台時,曾參與該次盛會。館內聘請之戲先生有苗栗的阿獅先、馮添財、李北海(小海)、陳西今、呂木村等人。光復後十年間,是共樂軒演戲最頻繁的一段時間,尤其光復後二、三年間,幾乎每個月演七、八棚戲左右,現今仍為台北八大軒社之一,演出則多為霞海城隍遶境之陣頭,近年已不再演子弟戲。 遊醬令與連清讚 根據筆者對北管曲牌的理解,遊醬令應為遊將令之誤寫,至此,推斷兩面皆為傳統北管常演之打牌子的鼓吹樂曲牌。 筆者所能辨認出來的兩個曲目為曲目中的流水板流水板,但是因為不同過場譜的使用以及不同派別在段落銜接手法上的差異讓筆者也不敢百分之百的妄論詳細的曲牌內容。 使用樂器為吹樂(包含噯仔、品仔)與後場打擊樂,但因為音質不佳,無法確定所用之下手樂器是否使用京劇武場下手,而極低頻的大鑼(子弟鑼)也因為考量到當時錄音技術的性能故先不予以討論。 吳漢殺妻 故事背景 原戲為《劉陽走國》,是敘述王莽篡漢,劉陽逃難的故事。全本戲包括討貢、敲金鐘、王英下山、探五陽、金蓮觀星、探妹、雙花會、擊山等。今「新美園北管劇團」常演。 《吳漢殺妻》,又名《斬經堂》。此戲敷為漢代故事,敘述王莽篡權後殺害眾臣,其中之一就是吳漢之父。吳漢長大後武藝高強,王莽為了重用吳漢,將他招為駙馬。吳漢鎮守潼關時拿獲劉秀,原本欲將劉秀獻給王莽,此時吳母告以王莽弒君殺父的往事,責令吳漢釋放劉秀,並將妻子王蘭英殺害,以報王莽殺父之仇。王蘭英為人溫婉善良,知道父親罪孽深重,於是長年在經堂內念佛消業。吳漢持劍進入經堂,見到妻子為了婆婆祝禱上蒼,一時不忍下手,王蘭英知道吳漢來意之後奪劍自刎,吳母因為逼子殺媳,也隨後自盡。吳漢縱火焚家,追隨劉秀而去。 唱詞內容 唱詞上 大花唱 本宮言來你細聽 大花白 宮主 正旦白 哎 大花唱 當初呀 大花、小旦同唱 哎(哭科) 大花唱 妻? 當初你父斬了我 的父妻子你年幼不知情 ? 殺父冤仇報得成 ? 三吋青鋒出了鞘 斬你首級見娘親 正旦唱 駙馬不必怒生瞋 妻子言來你細聽 當初你父□□□ 正旦白 駙馬 正旦唱 哎 駙馬 □□□□□□□ □□□□□□□ □□□□□□□
京劇與亂彈戲中的吳漢殺妻
台灣亂彈戲的《吳漢殺妻》屬於福路系統,其聲腔與徽調有些淵源關係。亂彈戲中《吳漢殺妻》的老旦唱【二凡】、正旦唱【平板】,徽劇中老旦唱【撥子】、正旦唱【吹腔】。 這齣戲在兩岸京劇界曾經因為「違背善良道德風氣」而遭到禁演,然而在台灣民間,《吳漢殺妻》卻是一齣膾炙人口的亂彈戲,職業戲班與子弟團皆常有演出。 在京劇中,賢慧的王蘭英終於決定一死,道出了三件遺憾之事(三不足),吳漢聞言深受撼動,於是打消了殺念,轉身欲回稟母親,此時王蘭英高叫「你看婆婆來了」,趁機奪下吳漢腰間寶劍自刎,吳漢大慟。但在亂彈戲中,孝字當頭的吳漢堅持要殺妻,甚至對妻子的求饒感到不耐煩: 旦:駙馬饒了吧,駙馬饒了吧!(生怒科) 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自刎科) 貼:啟稟駙馬爺,公主死了。 生:站開了!(科)公主!嬌妻!哎… 而亂彈戲中的吳漢舉止誇張、帶有狂態,為了取妻人頭而做出「三削頭」等身段,在快節奏的「鯉魚擺尾」鑼鼓聲中追殺妻子,有時又轉為柔情,在「慢長點」鑼鼓中與妻子難分難捨,到最後冷血地逼妻自刎,卻又大放悲聲。這段繁複而有點自相矛盾的表演,不禁讓筆者想到,《斬經堂》能在台灣民間劇場中久演不輟,也許觀眾就是要看架子花的誇張身段、正旦的恐懼(使用甩髮來表現),以及種種強烈的對比,包括心情的轉折與音樂節奏的弛張。 在唱腔方面,京劇中的《斬經堂》以上板的二黃板式為主,側重於敘事、說理,反之,亂彈戲中則以散板類板式來渲染情緒。例如,正旦昏倒在地唱【彩板】「聽一言嚇得我魂不在」,然後起身接唱【慢中緊】,這個板式類似於緊拉散唱的【搖板】,但伴奏不是類似垛板的有板無眼的板式,而是較接近一板一眼,有如京劇的【寬板】(寬搖板)。這種「慢拉散唱」的板式用在表現悲痛之情時,比起【搖板】或【散板】更為淒迷。 相關評論 ……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五)」中共樂軒的錄音是這些子弟團中水準較高的,《吳漢殺妻》中飾正旦、大花者的嗓音音域游刃有餘,唱到【緊中慢】時進入戲劇高潮,大花的嘶喊頗具劇場真實感,不愧是個具有豐富登台經驗的子弟團,這樣生動而情感豐沛的音樂風格,在今日以排場、清唱為主的子弟團之間,早已不易聽到了。…… 數位化與資料詮釋的省思 由於筆者曾經在幼時學過京劇演出,也在學習中國傳統打擊樂的過程中參與各種戲曲的演出,所以在筆者的認知當中,傳統戲劇的演出無論是唱詞、後場或者科白應該是有某種程度以上的規範與原則,就如同近期曾播映過之名角梅蘭芳的傳記電影中,即使是在表現的手法上想要做出一定效果以上的突破,對老一輩的演奏者們來說也是相當不能接受的。 不過再者兩片唱盤之中,由於這是此種表演藝術的嶄新呈現方式,讓記錄中呈現出來的成果與時下或者當的情形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詫異,是否是因為派別流傳,或者為樂師即興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或者可以從不同社會功能的角度來解讀呢?至此,我們只能期待有更多的解讀更多的資料讓我們有比對的目標或準則,也必須在解讀的過程中再加入更多不同流派、研究詮釋的校正,方不啻於讓這批歷史寶藏蒙上一層潽灰,而可以綻放他應有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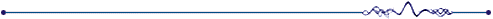
著作權所有 (c) 2009 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多媒體應用組。保留所有權利。
建議瀏覽環境:1024 X 768 螢幕解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