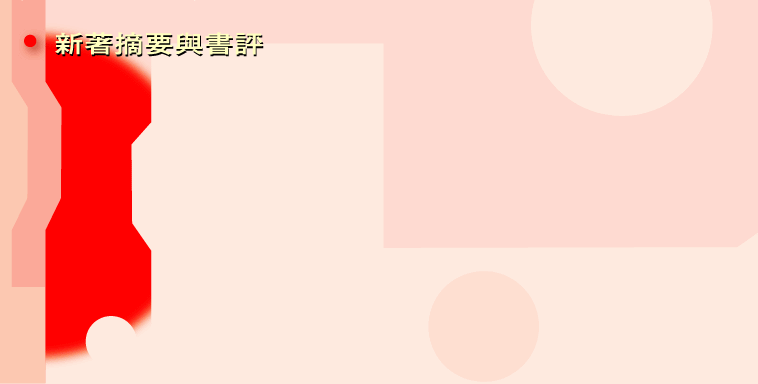紀錄攝影與紀錄風格
林志明 (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
前言
這篇文章的寫作動機來自兩個方向:
首先,在教學研究的過程?,我和學生們發現,紀實攝影、報導攝影(及它們其它的相關名詞如寫實風格、攝影人道主義、歷史攝影、新聞攝影)等名詞,在台灣的使用漸趨含混,造成了許多概念使用上的困難。這些概念區分的困難和必要,如何加以解決?由於最近歐洲學者所作的歷史性爬梳工作的出版,似已露出一道曙光。嘗試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兼顧攝影史和攝影批評發展史的雙元互動過程,顯然是一個十分值得嘗試的方向。面對這第一個問題,本文將以引介最近出版的一些文獻著作著手。
接著,經由去年一些重要的展覽發動,「紀實攝影」又再度回到美術館中,也引發了一些理論上的探討興趣。比如游本寬先生在去年瑞士《du》雜誌紀實攝影展時【註1】
為文提出的問題:「生活中,相同的影像出現在報上和消遣性雜誌中的認定是截然不同,更何況是『進入美術館』!傳統的美術館即使有社教任務,但主要仍是藝術成就表彰的場域。也因此,『紀錄攝影』進入其展示空間時,特殊的閱讀氛圍無形地誘導觀眾要多去體會拍照者如同藝術家般的主觀意識,而把影像的客觀、見証特質暫置一旁。『紀錄攝影』此時似乎已和影像紀實的使命無關,取而代之的是攝影者在圖象或藝術上的表現。」【註2】
攝影和傳統藝術概念本來在歷史上便具有的對立性,在這個交會點上顯得更為尖銳:紀錄性影像進入美術館中展覽,是否只是暫地被剝去了原有的特質,被人用另一個角度觀賞?或者,這所謂紀錄的特質,原來就可能只是攝影家所給予影像的一種外衣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認為,美國攝影家渥克·艾凡斯(Walker
Evans)所提出的「紀錄風格」(documentary style),可以是一個良好的思考起點。
紀錄攝影【註3】
的發展歷史
如果說,攝影史家大多同意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攝影的歷史是由形式主義走向紀錄風潮,這個演變的解釋卻似乎不是單純由社會運動和經濟危機的大歷史的角度可以完全說明的。1973年,John Zsarkowski便已指出這種解釋的問題點:「20年代使得那些最大膽的攝影家深感愉悅的抽象視覺遊戲,在30年代初期已喪失了大部份的魅力。因為我們對歷史對稱性的傾向,使得我們傾向將這個變化歸因於時代問題,尤其是社會政治意識的增強。不幸的是,這個解釋,雖然很迷人,卻和歷史事實逗不起來,因為後者不能証明在寫實主義及社會介入、或抽象和社會冷漠之間有什麼聯帶關係。…這個變化看來是在1930年左右進行的,而這基本上是一個形式上的演變 - 而且是這之前在攝影之中發生的事情的結果。」【註4】 由攝影內部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紀錄美學的發展應是在它被使用來為人道主義服務之前便已存在。」 【註5】
那麼20年代發生了什麼樣的重大轉變呢?十九世紀末起主宰攝影場景的「如畫風格」(pictorialisme)開始受到排斥,乃是大西洋兩岸共同的現象。在美國興起了由史提格里茲(Alfred Stieglitz)領導的「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註6】 ,在德國則有「新視象」(Das Neue Sehen)及「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由20年代中期起接踵出現,這是我們已經熟知的一段歷史。曾經編纂《德國攝影文選(1919-1939)》【註7】 的Olivier Lugon,在他的新著《紀錄風格:由桑德到艾凡斯》【註8】 一書中,結合了攝影史和攝影批評史的史料分析,對於德國的轉變歷程,作了一段精彩的爬梳工作。以大膽拍攝角度及抽象構圖試圖解放人類視象的「新視象」運動,在1929年的Fifo展【註9】 中達到高峰,但同時出現了由盛轉衰的警訊。它的大量發展及仿製開始被視為一種新的學院主義,甚至新的「如畫」風格 -- 這?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繪畫史平行的發展,雖然這一點Lugon未加以注意。雖然領導這個運動的Moholy-Nagy本身在包浩斯團體之中,而且他在包浩斯叢書中出版的《繪畫 攝影 電影》 【註10】也成為運動的宣言性著作,但1929年《包浩斯》期刊卻已刊出這樣的批評:「是的,人們普遍地把攝影和繪畫混淆在一起。情況因此和運動初期的情況是完全相同的。」【註11】 形式主義的企圖被認為取代了原來新觀看方式集體學習的宣稱:「關於根本性新視象的教育,當代的觀看知識,實際上沒有成為問題核心。至於由繪畫中解放,則更少被關注。」【註12】 「新即物主義」的單純、簡樸,逐漸地成為誇張、抽象的「新視象」的替代者。
這是一段逐漸走向客觀化的運動,但它的發展並不簡單。在「新即物主義」興起之初,法國的阿特傑(Eugene Atget)及美國的直接攝影曾經是它的雙重模範。但它們後來又成為「新即物主義」受到批評時的憑証:「這些影像中沉靜的單純性、明顯可見的潛沉觀照,很快地使得新即物主義中的奇觀裁剪,在對照下顯露出裝飾和人工性格。」【註13】 對於瞭解紀錄攝影的興起,最有效地莫過於回顧當時的批評。比如當時左派的批評:「不幸的是,這些布爾喬亞的『客觀』藝術攝影家遺忘了人,受苦的,被壓迫及鬥爭中的人。…『新即物主義』逃避現實,躲入抽象和形式遊戲之中,這個美好的物的世界,實際上一點都不是客觀的,因為它讓我們相信一小段無意義的世界影像便是『世界的影像』。」【註14】 (p. 56) 或是班雅明在〈攝影小史〉一文中的嘲弄態度:「在其中,展露了一種攝影的態度,想要給任何一個罐頭在宇宙中找一個位置,卻不能掌握人和人之間一丁點關係,而它非常飄渺虛無的主題,比較是在為它們的商業化而非認識作準備。」【註15】 如果說「新即物主義」的主要手法是特寫鏡頭,其藝術興趣是焦點的集中,那麼相對的觀看態度則呈顯為去聚焦(defocalisation):「以化約(reduction)獲得客觀性是容易的;以包融(inclusion)來獲得客觀性則困難多了。」【註16】 一個完全不同的觀看態度正在形成,它包括了框架的延展打開、攝影者主體的抹除、系列的運用、純紀錄功能影像的美學讚頌。 【註17】
也就是在這樣的思潮之中,使得桑德(August Sander)突顯為一整個新運動的代表性人物。雖然我們會感到桑德的作為,比較像是法國的阿特傑,是在一整套頗為傳統的,職業性的拍照過程中,似乎是無心地或無意識地演變成為一個紀錄攝影運動的領導人:如果說這一整個潮流重新使得「人像」這個攝影類型獲得復興,桑德的人像拍攝卻有一大部份是和他的謀生職業有關,而這也得他採取極為傳統的正面拍攝方式。以當時的語境及脈絡,Raoul Hausmann偏好使用「精確攝影」來和形容桑德:「總會有新人出現,以其鏡頭捕捉周圍世界的新觀點。現代攝影家很多,數目不斷增加,但沒有人曾想到Renger-Patzsch的客觀攝影已經被桑德的精確攝影所超越了。」【註18】 。在這個桑德在獲致和Renger-Patzsch同樣聲名的時刻,他其實年事已高(1930年時,桑德54歲),而且在生命之中已經經歷了重要的轉變,1910年他由Linz回到科隆,並且開始在鄉間尋找顧客。這個轉變使得他拍攝的社會領域擴展起來,同時也使得他在風格上脫離了所有和「如畫」風格有關的形式記號及布爾喬亞熱愛的室內景象:他「回到了表面上最傳統的人像攝影方式:明顯地擺好姿態,甚至顯得僵硬的正面拍攝人像,而且經常是在室外取像。」【註19】 桑德於20年代中期起進行的《廿世紀人類》計劃,嘗試以社會及職業範疇建立類型的計劃,已是為人熟知的中挫壯舉。但這?必須要補充有兩點,第一桑德為何有這樣的計劃,可能要回溯到20年代初期,他和科隆極左派進步主義藝術家之交往。他們的思維以去個人化、顯示社會權力關係為主軸,也把桑德推向了解析社會結構(因此是拍攝環境中的人)、清晰和中性化的路途之上。【註20】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桑德的大型拍攝計劃,除了社會類型人像之外,另一大部份是以這個社會的環境為主,由鄉村到最現代的大城市形成另一個系列。
這一份對人之環境的重視,其實也出現在新即物主義的代表性人物Renger-Patzsch身上:自從20年代末開始,他就突然由那使他成名的大特寫物件攝影中脫離而出,轉向拍攝社會現實甚至工人的住宅。他使我們看到的,正好是和早先的純粹性和構圖性相反的影像:這是一片巨大的、未聚焦的、人為和自然相交錯的、不知是鄉村或城市的曖昧風景。總的來說,風景其實是紀錄攝影所恢復的重要類型之一:由於它對包融性的注重、對拍攝對象的尊重和信賴,使得過去因為可能容易和「如畫」風格過度接近而遭到排斥的風景,又得到新的重視。但我們也必須說,這已是轉向一個以顯示人和環境關係為主的風景,而不是純審美的風景。
在這樣的回顧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紀錄攝影運動的美學要素已逐漸形成。它以包融的客觀性來取代聚焦的客觀性、強調拍攝者在對象前的中立性、並且著重系列的運用,影像以精確的呈現為主,主題面則重新開展出人和其環境的雙元主題。
紀錄風格
這一段歐洲的攝影史及攝影批評史,也快速地反過來作用在美國的攝影發展之上。1931年,時年28歲的艾凡斯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了以歐洲為主的六本當代攝影書籍,他在文章中對Edward Steichen的態度嚴厲,對德國新攝影運動有所保留,但熱情地表示桑德實現了「由阿特傑所預言的攝影未來。」【註21】
在美國的紀錄攝影發展歷程中,阿特傑是一位重要的引渡人。艾凡斯之外另一位重要的先驅者Berenice Abbott於1927年阿特傑死後購買了他遺留的大量作品,並於1929年將它們攜往紐約,隨後加以展出。於是就在1930年,Berenice Abbott和艾凡斯都取得了類似阿特傑曾使用的大型箱式攝影機,拍攝起阿特傑式的城市詩意觀察,對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事物、常民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等進行細膩的描繪 【註22】,並且展開了艾凡斯日後將之稱為「紀錄風格」新攝影美學。Abbott許下豪語:「尤金·阿特傑曾經為巴黎作的,也就是我要為紐約作的。」【註23】
關於「紀錄風格」,艾凡斯晚年曾在訪談中表示:「當你說『紀錄』這個字的時候,你的耳朵要足夠精細才能接收到這個字的意義。它意謂著紀錄風格,因為紀錄本意是一張警察拍的謀殺現場的照片。… 這才是真正的文件。你看到,藝術事實上是沒有用的,而一份文件就有它的用途。因此,藝術永遠都不是文件,但它可以採用文件的風格。我自己便這麼作。我被人稱作紀錄攝影家。但這預設著兩者間微妙的區分知識。」【註24】 。由影像風格的角度而言,艾凡斯自己曾經下過這樣的詮釋:「我真正在談的是事情具有純粹性和某種嚴厲、嚴謹、單純、直接、明白,而且它不具有藝術家的企圖,不過這是指這個字的自覺意義而言。它的基礎在此 - 它們是堅固結實的。」【註25】 因此,「嚴厲、嚴謹、單純、直接、明白」是其風格特徵,但,這是怎麼樣的影像呢?是否能有更精確的分析描述方式?另一方面,除了影像本身的分析,由艾凡斯的工作態度與方式(就這一點而言,Newhall在1938年所提出的「紀錄取徑」documentary approach 【註26】,毋寧是更適合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獲得更進一步的瞭解。
Lincoln Kirstein 曾經如此描述艾凡斯拍攝建築物時的工作方式:「為了用使得細節能夠展現出最堅實的浮雕效果,他只能在明亮的陽光下工作,而且要站在街道正確的一邊。有時為了拍一棟房子,必須去好幾趟,以避免樹本或其它房子的陰影;只有春天和秋天才是適合的季節」。【註27】
除了這樣的工作方式及態度之中所內含的等待及觀察,我們也知道艾凡斯使用過許多不同的攝影機並且對同一個對像進行多次的拍攝:他總是希望能在拍攝之後能加以選擇,甚至裁剪。對於同一個對象,他甚至使用了不同的相機和不同的鏡頭 【註28】。在這?,我們可以首先推導出他對世界的曖昧性或多重關係希望有所保留的態度:在不同關係的建立之中,同一個對象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每一次不同的取景和景深運用,便會帶引出不同的觀看。再進一步,艾凡斯此舉實已使他自己成為其照片的編輯者,而他的「紀錄風格」,也是在這些選取之中,逐漸地累積出來。雖然本身曾經想嘗試成為作家 【註29】,也曾經寫作過許多攝影文論,但艾凡斯不是一位以計劃和宣言等概念為前導推動創作的攝影家,這一點顯然和歐洲前衛攝影家的氣質有許多的不同。
最後,為了說明艾凡斯「紀錄風格」觀念所包含的可能變化,以及美國紀錄攝影的持續演變,我們必須對著FSA(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美國農業安全部門)計劃和這個問題的相關性作一個簡短的交待。艾凡斯在FSA計劃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實際的執者之外,更像是團隊的總教練。【註30】 但艾凡斯不但在中途離開了FSA計劃,就數量上來講,他的生產,也不是其中最顯眼者。【註31】 艾凡斯後來回憶說:「[Stryker]保留了那些利用我的風格的人,但卻教我走路。」【註32】
艾凡斯這句看似平凡的話,有其許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它顯示出「紀錄」可以是一個進行不同使用的「風格」,而這也種下了今天我們在「紀錄」、「紀實」、「報導」攝影、乃至「人道」、「寫實」攝影等多種名詞之間難以精確分辨的根源。【註33】 「紀錄風格」所產生的真實感只是一件外衣,如果要加以深究,則不得不進入更細緻的意圖、方法、步驟甚至主題的分析。FSA計劃後來的發展,正是一個良好的說明。它基本上走向了許多和艾凡斯基本態度背道而馳的方向:以人道關懷為名義的弱勢者圖像,著重照片所引起的感情效應、以報導為主導的模式,著重影像和文字間的資訊整合甚至「拍攝腳本」(shooting script):拍攝前的指導和事後的影像剪輯。這種以良好說故事影像(good story-telling pictures)【註34】 為主要目標的方向,和艾凡斯著重的「非個人性、系統性和正面性觀看」已經相離甚遠,但它迎合了當時正在興起的影像畫刊媒體的發展潮流(如1936創刊的Life,1937年創刊的Look),將美國的紀錄攝影,推向了人道報導攝影的境地。【註35】
結語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並且嘗試回應作為本文出發點的問題:紀錄攝影的發展,由阿特傑、桑德到艾凡斯手上,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美學風格。因為曾在德國和20年代前衛派交手,使得它著重包融的視野和非個人的觀看:或者說一種作者消隱的態度 - 但由艾凡斯的工作方式中,我們知道這所謂的消隱,乃是一種精鍊的過程。由於在歷史的發展過程?,它曾和報導攝影的興起有過重疊,甚至作為其源起的根基,也造成了我們今天概念難以釐清的窘境。筆者這篇短文,借用了歐美學者研究攝影史和攝影批評史的發掘成果,期待能引介此一問題的歷史性因緣探討取徑,使討論不再只是在文義或定義上轉動。
---全文完
【注釋】
【註1】關於2002年春在北美館舉行的「時代的見証:1941-1995紀實攝影展」之背景介紹及評論,請參閱蕭永盛,「我們由廢墟?站起來,卻又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記《du》雜誌與『時代的見証:1941-1995紀實攝影展』」,台北,《現代美術》,No.
101, 2002年4月,pp. 14-17。同年夏天另一個和紀錄攝影相關的展覽則是北美館周慶輝「消失的群像:勞動者記事」,可參閱《現代美術》No.
103,2002年8月許綺玲文。
【註2】游本寬,「拍照記錄的藝術」,台北,《現代美術》,No.
101, 2002年4月,p. 26.
【註3】我這?指的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或法文la photographie documentaire, 台灣一般亦作紀實攝影。由於「紀實」容易引起一些概念上的問題(比如究竟是那一個層次的真實),所以決定追隨游本寬的譯法,稱作「紀錄攝影」。游本寬在前引文開頭已對這個名詞的出現作了一些追索。我們可以補充的是除了Beaumont
Newhall所引1926年John Grierson談Robert Flatherty紀錄片Moana文章之外,此字的相關用法在法文中已於1906及1915年出現,也是以電影為對象。至於這個字眼被用來談論攝影,則確定在1920年代末出現於法國及德國,稍晚於1930年在美國出現。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Paris, Macula, 2001, pp. 14-15.
【註4】John Zsarkowski, Looking
at Photographs. 100 Pictu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3, p. 116.
【註5】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32.
作者表示,這個觀點在1939年已為Steichen看出, 同時20年代對社會政治的反應,則多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進行。
【註6】Straight 這個字有許多意味,比如「正直」、「無保留」、「純淨」、「未變更」等。
【註7】Olivier Lugon (ed.), La
Photographie en Allemagne, Anthologie de textes, 1919-1939, Nimes, Ed. Jacqueline
Chambon, 1997. 同一年代法國方面的攝影批評史資料請參看 Dominique Baque (ed.), Les documents de
la modernite, Anthologie de textes sur la photographie de 1919 a 1939, Nimes,
Ed. Jacqueline Chambon, 1993.
【註8】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註9】這個展覽全名為Film und Foto,1929年春首先在司圖嘉舉行,接著巡迴展出。
【註10】Laszlo Moholy-Nagy, Malerei
Fotografie Film, Munich, Albert Langen Verlag, Bauhausbucher no 8 ; 1925 (2e
ed. 1927).
【註11】Friedrich Vordemberge-Gildwart,
"optik - die grosse mode", bauhaus, vol. 3, no 4, oct.-dec. 1929.
(法譯見Olivier Lugon (ed.), La Photographie en Allemagne, Anthologie de textes,
1919-1939, op. cit., p. 198)
【註12】Goerg Paech, "Der
neue Fotograf", Dresd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5 sept. 1929. 轉引自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42.
【註13】Ibid., p. 52.
【註14】Heinz Luedecke, "Schulter
an Schulter", Der Arbeiter-Fotograf, vol. 4, no 12, 1930.(法譯見Olivier
Lugon (ed.), La Photographie en Allemagne, Anthologie de textes, 1919-1939,
op. cit., p. 292.)
【註15】Walter Benjamin, "Petite
histoire de la photographie", in Oeuvres II, Paris, Gallimard, 2000,
p. 318.
【註16】Katherine Grant Strene,
"American vs. European Photography", Parnassus, vol. 4, no 3, Mars
1932. 引自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58.
【註17】Ibid., pp. 58-67.
【註18】Raoul Hausmann, "fotomontage",
a bis z, no 16, may 1931.(法譯見Olivier Lugon (ed.), La Photographie en Allemagne,
Anthologie de textes, 1919-1939, op. cit., p. 232.)
【註19】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68
【註20】Ibid., p. 71.
【註21】Walker Evans, "The
Reappearance of Photography", Hound & Horn, vol. 5, no 1, oct-dec.
1931. 本文重印於 Unclassified. A Walker Evans Anthology, ed. by Jeff L. Rosenheim
and Alexis Schwarzenbach,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註22】艾凡斯曾於1926年至1927年居住於巴黎,他早期的攝影作品仍受當時歐洲前衛攝影的影響。即使1928-1929年左右返國後,他初期開始大量拍攝紐約時,也以金屬結構、特殊取角等新視象的風格進行。比如著名的布魯克林大橋系列(1929,主要以21/2x41/4的捲軸底片進行)。參閱Walker
Evans at Wor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1994, pp. 40-41.
【註23】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81.
【註24】"Katz/Evans interview",
Art in America, April 1971. 引自Walker Evans at Wor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op. cit., p. 216.
【註25】Walker Evans, "Lyric
Documnetary", Lecture at Yale, 3/11/64. 引自Walker Evans at Wor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op. cit., p. 238.
【註26】Beaumont Newhall, "Documentary
Approach to Photography", Parnassus, vol. 10, no 3, mars 1938.
【註27】Lincoln Kirstein, 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Dec. 1933. 引自Walker Evans at Wor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op. cit., p. 50.
【註28】Jerry L. Thompson, "Walker
Evans: Some notes on his way of working", in Walker Evans at Wor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op. cit., p. 10
【註29】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福婁拜。
【註30】他在其中職稱是Senior Information
Specialist,實際上也為總負責人Roy Stryker作coaching的工作。
【註31】在目前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FSA檔案中約共有七萬五千張照片,其中艾凡斯只佔數百張。Jerald
C. Maddox, 'Introduction", in Walker Evans: Photographs for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1935-1938, US, Da Capo Press, 1973, p. ix.
【註32】Olivier Lugon, Le style
documentaire : d'August Sander a Walker Evans, 1920-1945, op. cit., p. 100
【註33】使得這個問題更複雜的還有社會科學如視覺人類學或視學社會學的影像使用。參閱Howard
S. Becker, "Sociologie visuelle, photographie documentaire et photojournalisme
: tout (ou presque) est affaire de contexte", Paris, Communications,
No Spe. " Le parti pris du documents : Litterature, photographie, cinema
et architecture au XXe siecle ", No 71, 2001, pp. 333-349.
【註34】這是Edward Steichen 1939年在US
Camera為FSA 專刊作導言時的用語。見ibid., p. 105
【註35】除了多次直接表達他對報導攝影家Margaret
Bourke-White書中呈現的感傷與煽情表示不屑之外,艾凡斯1938年陪伴其MoMa個展所出版的《美國影像集》(American Photographs)在編輯製造上也有意加以區別:避免文字和影像的連結、並且以置身現代藝術傳統為企圖。參考Jean-Fracois
Chevrier, "Walker Evans, American Photographs et la question du sujet",
Paris, Communications, No Spe. " Le parti pris du documents : Litterature,
photographie, cinema et architecture au XXe siecle ", No 71, 2001, pp.
62-64.